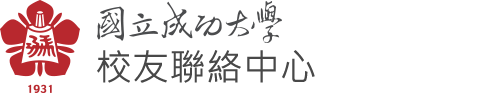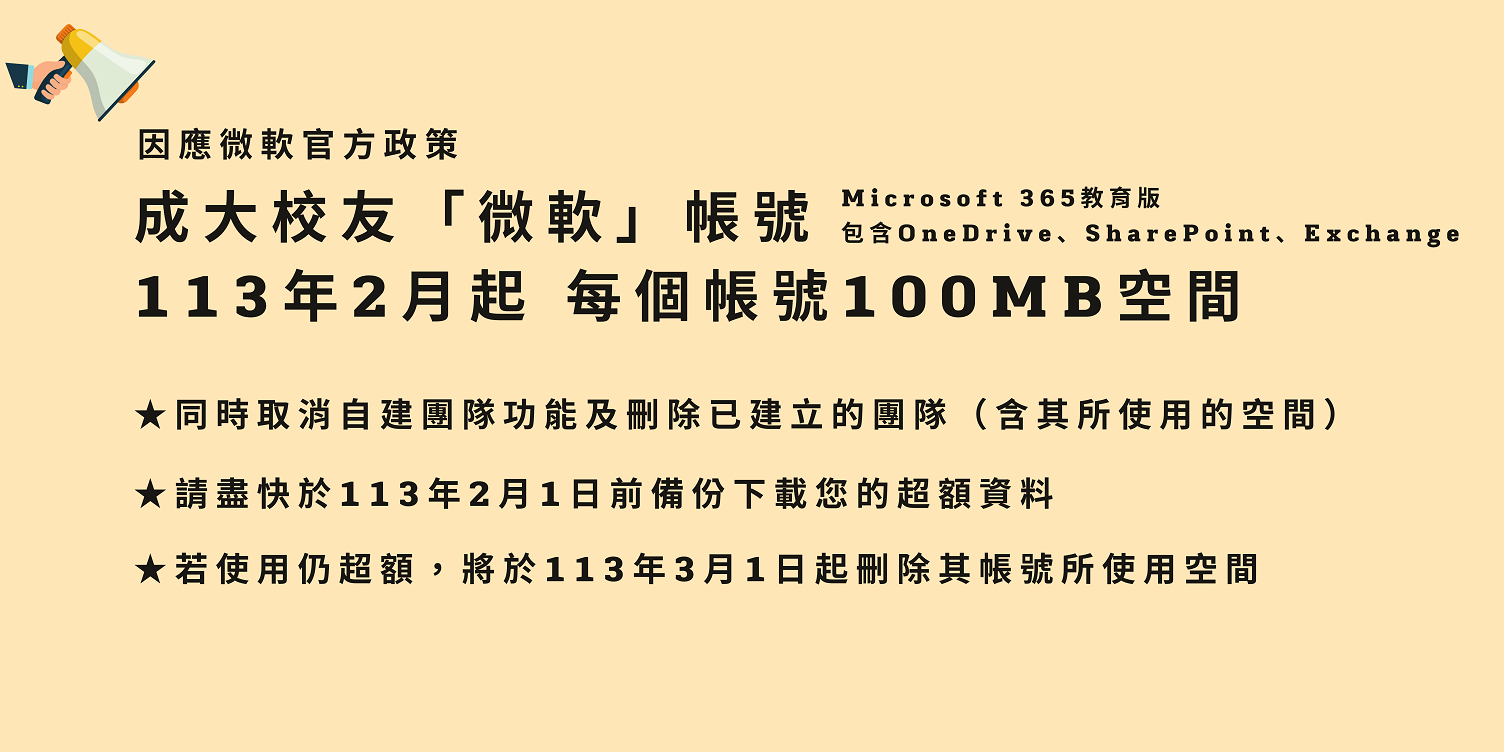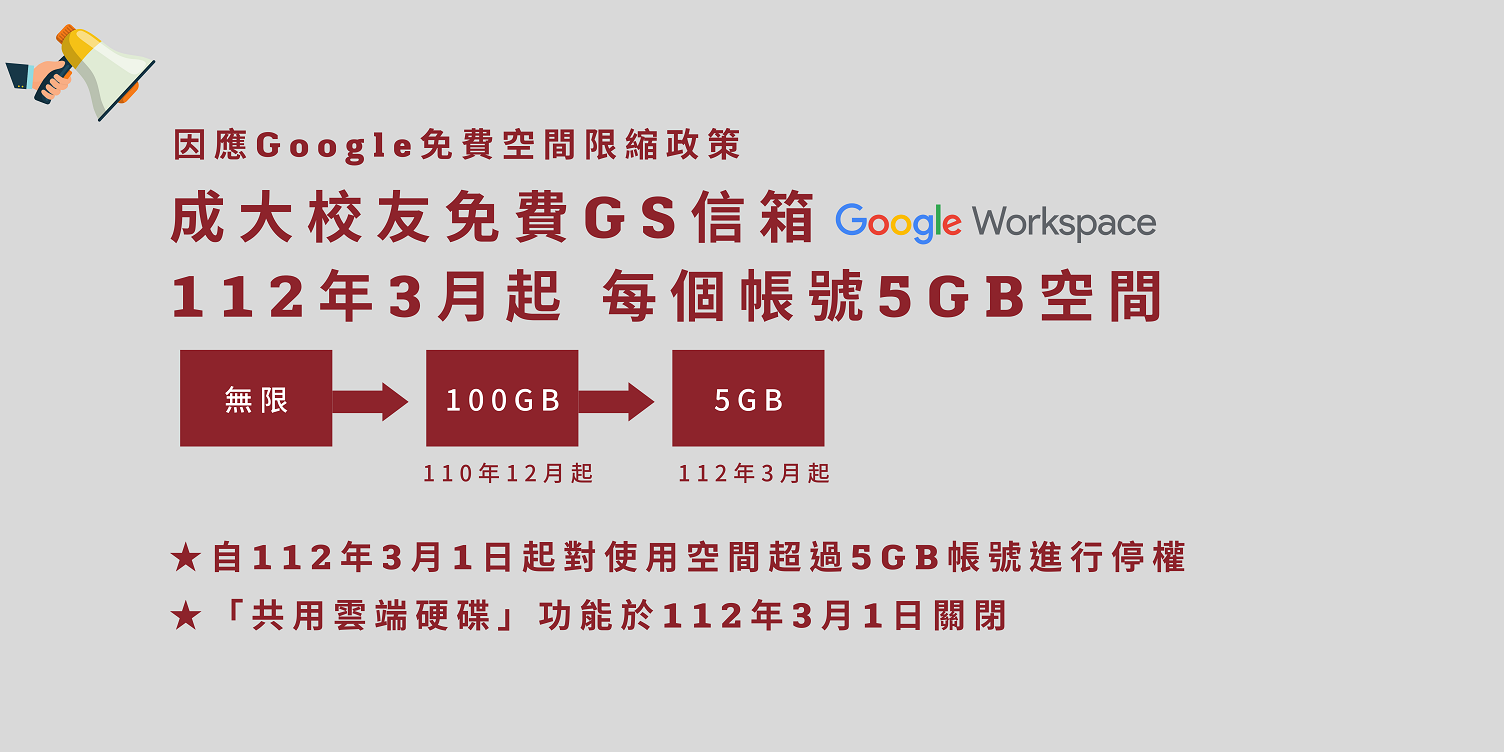學術界的空手道強人:李仲森自信挑戰挫折
李仲森是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旗下地理遙測學會(IEEE GRS-S)成立20多年來,第三位獲最高榮譽的「終身成就獎」的華裔科學家。最早從事自動控制工程專業,而後轉入衛星遠距遙測研究,在研發以綜合口徑雷達(SAR)提供更準確的地理遙測資訊方面,享有崇高聲譽。然而除去學術研究的光環,李仲森同時也是一位教學長達20多年、深受學生與家長愛戴,並尊稱為「Sensei Jong-Sen」的空手道老師……
回望榕樹
這幾年,成大發展得很快。許多新建築冒了出來,還記得以前光復校區住的都是軍人,門口總有警衛守著,學生絕對不可能進去。……今天早上我到榕園去散步,才發現:大榕樹長得真漂亮!
回憶起成大,最令我驕傲的地方是圖書館(現在的K館),當時有朋友到成大來,我一定先帶他去參觀圖書館;第二個就是成大電機系,成大電機系的設備是全台灣第一好的,甚至比台大要好上許多。所以高雄中學畢業後,我選擇保送到成大電機,而不是去考台大或者醫學院。
那時系主任周肇基老師非常嚴格,他所教授的電子學,每次考試至少都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。不只他,系上每位老師都嚴厲把關著我們的學習成績,大一入學時有一百位同學,其中也有多位僑生,但只有七十幾位能夠順利畢業。學期成績有八十幾分就算很不錯了,因為老師的問題都很困難,不過大家總是非常用功,加上當時成大四周都是農田,沒有什麼休閒娛樂,有些同學甚至連運動會都不參加,我自己倒還會去跑跑步,放鬆一下。
扎根基礎科學的成就
後來我到哈佛攻讀碩博士,發現台灣學生在基礎科學方面的能力比較欠缺,知識領域也不夠廣,只知道自己學的那門科學,其他都不清楚。然而不管是創業或是研究,或多或少都會涉及各領域,好比我是學控制系統的,但後來做的工作卻和控制系統沒關係,這時基礎科學就顯得非常重要。數學、物理都是基礎科學,以我們電機系來說,統計學也很重要。
哈佛規定學生不能只專修一科,希望我們多學習其他東西,那就是通識。通常要有一個主修和兩個副修,主、副修的領域不要太接近,這樣將來碰上了,就有機會派上用場,當時我其中一個副修就是物理的量子力學。
在台灣很少有老師跟我們提醒這些事情,一直要到出國才感受到,特別是統計學。很多物理現象都需要用統計學解釋,如果沒有統計學的基礎就沒辦法了解,雖然我們也學了一些矩陣的東西,但因為學得不夠深,到哈佛之後才發現自己只是一知半解。別人懂、你卻不懂的話,是很吃虧的,所以我總是要花比美國學生還要多的時間跟上進度。
昨天我回電機系演講,談我在美國的經驗,題目是「Pursuing PhD and conducting research in US」。主要談的就是做研究一定要有扎實的基礎科學,其次,要找對研究題目,最好是新興的領域。這是因為新的領域能做的東西很多,假如等到大家都做得差不多以後,那些比較重要的題目已經都被做完了,你只能跟在後面改良別人的東西。
當然也要盡可能往對社會有貢獻的方向研究,有貢獻之後,就能夠建立權威,有權威以後,能夠取得的研究資源就更多、也更容易。如果可以找到一個全新的領域當然很好,加上好的基礎科學,就容易進入研究;如果還是你原本領域內的研究,那麼盡量從原有的問題中去發掘新的概念,找一個新的概念比推導一個公式還更重要,從舊的問題發現新的題目也很好。
我大學論文的指導教授是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,他曾經看過有人研究了一整年卻沒有任何進展,於是告訴我:「做研究是要廢寢忘食的,你睡覺的時候、走路的時候、吃飯的時候都要想它,你一天到晚想的話,就有機會豁然貫通,或發現有什麼部分可以去試,也說不定你找個朋友談一談、解釋給他聽,你就會發現自己沒有注意到的盲點。」他說:「You have to sleep with it。」所以後來每當我有問題想不通時,就去外面走走,一邊走一邊想。
用英文能力走進國際
我們那個年代學英文是很不容易的,到美國後最挫折的就是英文能力不夠好,該怎麼表達自己的想法?怎麼跟對方溝通?怎麼跟美國人交朋友?這些都不太容易。在台灣想學英文我們只能聽「趙麗蓮空中英語教室」,或去看兩場電影,第一場只是單純享受情節,第二場才試著去仔細聽英文。
本來以為自己英文算不錯了,出國後才知道還差一大截,只能慢慢學,幸運的是在美國學進步比較快。博士學位資格考試的時候,哈佛沒有筆試、只有口試的。華人筆試沒有問題,口試卻容易緊張,一緊張就完了,聽不懂對方在問什麼,不光我們有這種問題,就連印度來非常聰明的學生,也覺得口試是一大挑戰。
所謂的口試,通常是你站在台上,下面會坐著四個教授,一個是你的指導教授,另外三個則由指導教授找來,通常和你的領域都不相干。他們並不針對你的論文發問,而是給你一個問題,看你如何解決問題。美國的學生經常需要上台做專案報告,台灣學生則蠻欠缺這方面的訓練,只會考試。就因為這樣,我第一次的資格考試沒有通過,幸好教授他們看我成績這麼好,卻考不過,心想一定有原因,決定再讓我重新考一次。後來我就專心準備了三個月,讓心情穩定下來,思考他們問題的方向是什麼,後來才總算通過了!
我因為在這些地方遭遇挫折,所以學到更多東西,挫折不見得是壞事,說不定反而可以開發出一片新天地,這都是很好的經歷。
常春藤盟校包括:布朗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、康乃爾大學、達特茅斯學院、哈佛大學、賓州大學、普林斯頓大學、耶魯大學等八所學校。這些大學招收學生的標準主要是看你在學的名次,假如你是電機系第一名畢業,進去的機會就大很多,我當年僥倖以第一名畢業,所以到哈佛後就能拿獎學金。
說起來慚愧,我是因為拿到了獎學金才決定要去留學,在那之前本來只是想申請看看,確定拿到獎學金之後,我才開始準備考試。先到台北的美國大使館考試,接著口試,都通過之後我就到美國去了,並沒有花太多時間準備。學弟妹想申請出國的話,就跟我一直強調的基礎科學和英文一定要學好。
跨領域、國際的學術研究
兩年前我從任職超過37年的美國國防部海軍研究實驗室(US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)退休,是因為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請我回來當客座教授,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希望利用退休的時間寫一本書,因為擔心一個人寫的時間不夠,所以也找了法國Eric Pottier教授共同出版,書《Polarimetric Radar Imaging: From Basics to Applications》已經在今年(98年)二月出版了,是一本非常有用的教科書。
從事研究的人一定要想辦法跟別人合作,雖然不見得一定要在成大,但在成大跨系合作也很好,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。我自己則是跟很多不同國家的人合作,例如Eric Pottier,跟他說要一起寫書已經談了五年;也跟法國、德國、義大利、丹麥、台灣等地教授合作發表論文及研究成果。越和他人合作,在那個領域就越容易受到重視,也因為每個人想法都不同,所以可以擦出不同的火花。多參加國際會議,就可以慢慢的建立自己的人脈,找到適合一起工作的夥伴。
有時候也不見得是你去找人,說不定是對方來找你,這時候建立自己的信譽就顯得很重要。開始學習的時候,通常是指導教授或跟你一起工作的人給你指點。不過,一旦有機會參加國際會議時,就要盡可能找已經建立權威的學者討論,他們通常非常親切、不會擺架子,不懂的問題都可以跟他們請教;或是你拿一個解決了差不多的問題跟他談,說不定他能給你一些新的點子,然後問他願不願意讓你把他的名字放在你的論文上面,兩個人合作共同發表,當然他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頭,但這卻表示他已經認同了你的觀點,無形中,也建立了你自己的人脈,這些都是我給想從事研究的學弟妹的一些建議。
嚴格的空手道老師
我在華盛頓除了工作外,業餘時間在華府、慈濟、博城等中文學校及「竹濤社」義務教學空手道,已經二十多年了,每個禮拜要教三次,每次教兩到三個鐘頭。我們盯的比外面還要嚴格,至少會失敗個兩次、花上八、九年的時間才拿到黑帶,這是告訴學生:「人生不會總是那麼平穩,一定會遭遇挫折,能不能在挫折中重新站起是非常重要的。」我們教出去的學生都非常優秀,哈佛、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都有。那是因為只有優秀的學生才可以畢業,他們都有著奮戰到底(fighting to the end)、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。
我因為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那上面,所以沒有時間去接觸校友會。不過,這次回台灣改變了我不少的想法,之後會跟華府校友會多接觸,聽說他們活動很多,也有很多我認識的校友,應該會感到很親切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