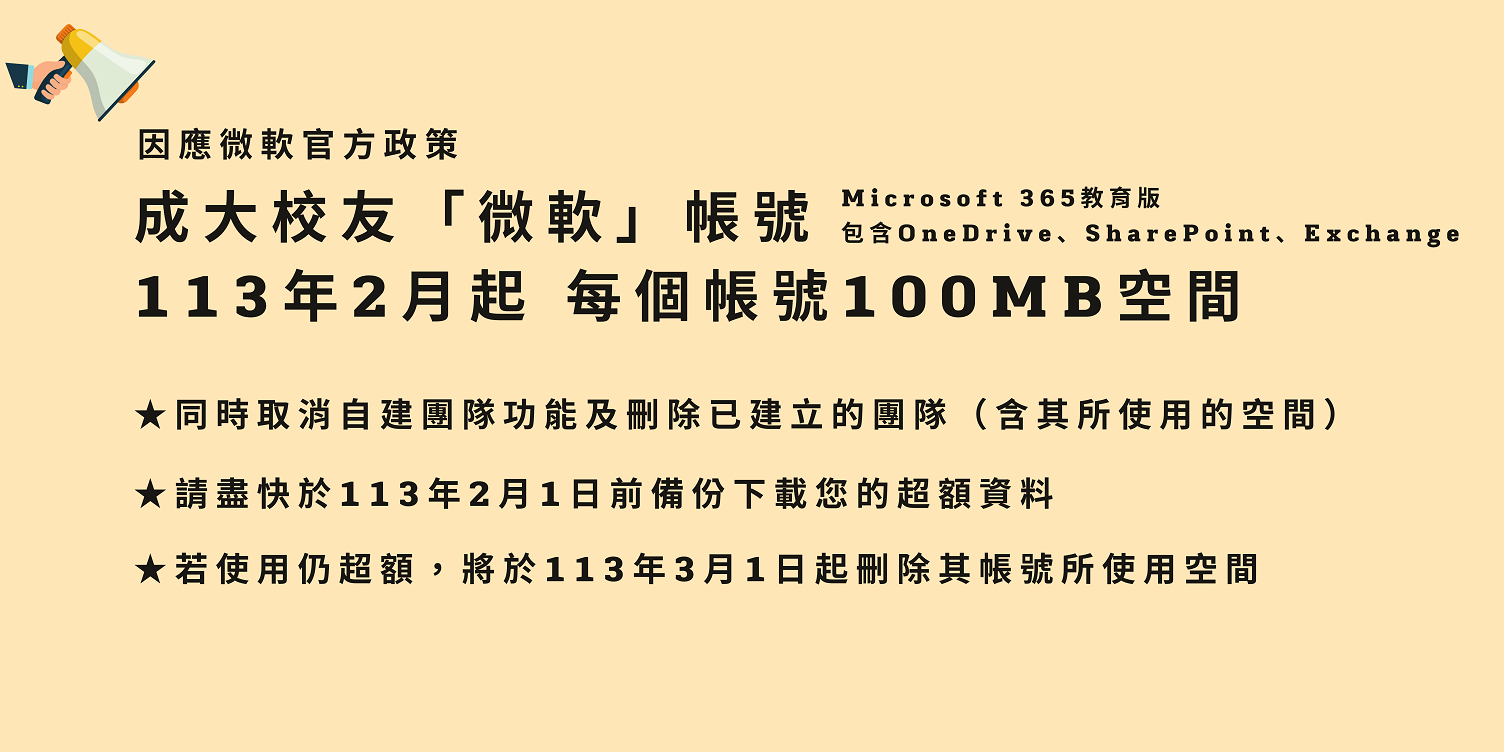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
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
歷史系教授 林瑞明
第一個把白話文的真正價值具體地提示到大眾之前的,便是懶雲(賴和)的白話文學作品。在一個文言文的世界中,以先人所以為淺薄粗鄙的白話文為文學表現的工具;寫大人先生輩以為鄙野不文而唾棄的小說,不能不說是一種大膽的、冒險性的嘗試。而由於他的創作天才和文學上的素養,幸而成功的完成了這個嘗試,並且多少給予白話文陣營以自信,並煽起無數青年對於「小說」的熱烈的
愛好。
這是日治時期,楊守愚在「賴和先生悼念特輯」,給予賴和的評價。
賴和是仁醫,也是日治時期著名的社會運動者,從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,一直以文化抵抗的方式,堅決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。
台灣新文化啟蒙時期,賴和是將「現代以前之學藝文化」轉變為「現代性學藝文化」的重要推動者之一。賴和以他的新文學創作,首先奠定台灣新文學的基礎,並深遠影響同時代及後一輩的台灣作家,形成蓬蓬勃勃的台灣新文學運動。在他生前,即以文學成就被文學界尊稱為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。
賴和的文學,當然一部份由於他的天分,一部份受到五四新文學思潮的影響,得風氣之先,而更重要的則是透過社會運動實踐而來,所以他的文學與時代有密切的關係。
賴和十歲時先被家人送入書房學習漢文,然後在日本政策下始入公學校「讀日本書」,每天早晨上公學校之前先上書房早讀,下課後再到書房上課。十四歲入小逸堂拜黃倬其為師,而這使得賴和具備了寬廣的文化視野,對於未來路線,有極深刻的影響。十六歲時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,結識了翁俊明、王兆培、蔣渭水、杜聰明等人,而這也使得他與台灣文化抵抗的運動,緊密的結合起來。
回溯賴和文學修持的過程,早年小逸堂等書房的漢文教育,是他能寫傳統詩的重要根源,並創作出相當多的作品;值至青年時期,他已涉獵大量的外國小說,甚至在獄中亦申請看〈噫!無情〉、〈紅淚影記〉等;透過翻譯的西方文學,新文學的種子,已在等待著適當時機發芽生長。
由目前所清理出的遺稿及發表稿中可得知,賴和約在一九二二年左右,已開始在練習白話文的寫作。從現有的資料裡,得知最早的一篇可能是〈祝南社十五週年〉的祝賀詞。
世間話說的好,
詩是無用的東西,寒不會禦寒,飢不會療飢。
那仙的李白,聖的杜甫,究竟何補些兒?
是是飢要覓食,寒要覓衣的,
實在用他不著,也就可以付之不知。
咳我且問汝,誰叫汝們會寒會飢?
汝們可曾偷懶過呢?
我們做詩的亦還不衣會寒,不食會飢,就是做苦來過日子也廢不了做詩。
為甚麼呢?有的、愁嘆的聲、傷悲的淚、歡喜的情、感憤的氣,一條鞭寄在裡頭去。
況又是通聲氣,同環境的人自然會聚攏在一塊兒。
貴社創立過十五年了,
社況的盛大,社運的發展,久為我們所共知
南都文化的精血盡傾注在這裡,
問精神的發露就在一一詩一一
我希望大家們實地裡做詩人,生活去使這無用的有用,教他不知者共知。
為我們作詩的吐些兒氣,
那始不負我們
用盡心力來做詩。
這一篇作品,文白夾雜,用了一些語助詞(如「兒」、「呢」、「了」)來增加白話的氣氛,因為文白夾雜,念來十分拗口,有些地方語意不清,這正也顯現出台灣新文學的出現是多麼不容易。此外,更在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四年的傳統詩稿本中,發現賴和二十多首的白話詩作品,我們知道賴和的新文學運動,起步相當的早,僅隔三年,賴和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發表的第一首白話詩〈覺悟下的犧
牲) ,我們看見了賴和在新文學上的努力。
賴和對白話文的運用,遠溯在醫學校時期學過國語正音,廈門博愛醫院的那段期間可能亦學習過,此外從賴和藏書中收有〈小說月報〉、〈語絲〉等(此兩份雜誌,皆是帶動中國新文學運動發展的重要刊物) ,以及訪問賴和五弟賴賢穎得知,還可能是透過閱讀中國新文學作品而來。
台灣新文學是由白話文出發,賴和得風氣之先,將一九二0年以後的文學理論,具體化地呈現出來,由他「打下第一鋤,灑下第一粒種子」。我們從他早期發表的作品,再一次檢討白話文使用的問題,可以肯定地說,賴和以他辛苦磨練來的中國白話文基調,加上不可或缺的台灣色彩,以作品更進一步帶動台灣新文學的風潮。舉例來說,在〈鬥鬧熱〉開頭一段寫景的場面:
拭過似的,萬里澄碧的天空,抹著一縷兩縷白雲,覺得分外悠遠,一顆銀亮亮的月球,由深藍色的山頭,不聲不響地,滾到了天半,把她清冷冷的光輝,包圍住人世間,市街上罩著薄薄的寒煙,店鋪簷前的天燈,通融化在月光裏,寒星似的一點點閃爍著。
這完全是中國白話文的語調,由遠景拉到進景,然後帶入即將呈現的事件。賴和白話小說的描寫能力,已經相當成熟了。此外,賴和也一再運用褔佬話、俗語、諧音使得全篇小說具有台灣地方特色。例如:
1 、囝仔事惹起大人代。
2 、狗屎埔變成狀元地。
3 、儉腸捏肚也要壓倒四福戶。
這使得賴和的小說更具親和性。然而由於語言運用的問題,賴和寫作的過程,極為辛苦。王詩琅在〈賴懶雲論〉裡,留下一則記載:
他是一個極為認真的作家。每寫一篇作品,他總是先用文言文寫好,然後按照文言稿改寫為白話文,再改成接近台灣話的文章。據說也有時反其道而行的。然而也因之他的作品也顯得十分工整。這些話透露了賴和那時代的人,應用白話文寫作不是那麼簡單的事,賴和以些許國語正音的能力,透過了閱讀五四新文學作品,培育了中國白話文寫作能力,才能在台灣新文學的領域首先開拓,並得到廣泛而肯定的評價。
爾後賴和擔任〈台灣民報〉的編輯,以編輯者的身份介入新文學運動,對於文學發展的方向,更具影響力。賴和的編輯工作十分吃重,就如同在一片荒蕪的園地裡開墾,以便培養出各種奇花異草。楊守愚極為瞭解箇中甘苦,在他的回憶裡,留下了一段相當重要的記錄:
他當時幾乎是拼了老命去做這份工作的。他毫不珍惜體力的去一一刪改寄來的稿子,有時甚至要為人改寫原稿的大半部份。常常有些文章,他簡直是只留下別人的情節而從頭改寫過。
賴和的新文學活動,可以從目前可知賴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發表的第一篇隨筆〈無題〉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的台灣話文小說〈一個同志的批信) (從目前已出土之楊守愚日記得知, <赴了春宴回來〉為楊氏以賴和之名代撰的) ,前後約略十年。除了在一九三六年為李獻璋〈台灣民間文學〉作序,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,在〈礦溪〉創立廿五週年紀念號發表〈輓李耀燈君〉以外,賴和的文學重心,多放在漢詩的寫作上。這或許是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台灣總督府強制〈台灣新民報),(台灣新文學〉廢除漢文欄,賴和又堅持用漢文創作,以英雄無用武之地,停止新文學的創作,以文化遺民的精神寫傳統詩,正是文化抵抗的姿態。由這個角度來理解賴和的新文學活動,更突顯出他所具有的特殊意義,但賴和停止新文學創作,是否尚有另外的因素,亦值得進一步探究。
賴和的作品是由現實出發,透過寫實主義與藝術的關照,深刻表現日治下台灣殖民地的眾生相,尤其是一群被壓迫的弱者,從而強烈地表現了「我值強權妄肆威」的時代,也傳達了「被侮辱人勝利基」的訊息。綜合的來看,賴和一方面從文化革新的角度,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(如〈鬥鬧熱〉、〈蛇先生〉、〈未來的希望〉等) ,一方面由弱小民族抵抗的立場譴責統治者不義的法(如〈一桿「稱仔」) 、〈豐作〉、〈補大人〉等)。透過弱者、被壓迫者悲慘境況寫實面的描寫,賴和的文學控訴,顯得強而有力,也傳達出時代的心聲,屬於積極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抗議文學。
賴和客觀地觀察台灣的各種社會現象,以冷靜的態度來塑造小說世界裡的人物。在他的小說裡,看不見救贖式的人物,一般人都是能忍則忍,如〈豐作〉、〈一個同志的批信)。<一桿「稱仔」)在原稿中,秦得參是以自殺作為結束,但在發表稿中秦得參卻是與欺壓他的警察同歸於盡,這顯現出賴和在創作過程時,理想與現實在內心的掙扎。儘管賴和以這樣激烈的行動來表現出殖民地人民的憤怒,但這種個人的行為,即使報導恐怕也會被曲解,壓縮在新聞的一個角落。在賴和的小說裡,我們看見一群被舊社會的有利者不管經由什麼方式壓迫下的弱者,也看見被日本殖民統治者恃法壓迫的人民,這正是賴和生存時代的寫照,他以他的文學作品客觀表現了出來。
在詩的表現上,賴和通常經由客觀的事件,在發展的過程中表達了他強烈的意念,如〈覺悟下的犧牲一一寄二林的同志〉寫的是二林事件, <南國哀歌〉寫的是霧社事件。賴和強烈呼喚著人民「捨此一身和他一拼」,因為所要追求的不是眼前的幸福,而是後代千千萬萬子孫的幸福,只有不懼死亡,才有再生的希望,這正是賴和文學的精神;而所呈現的道德勇氣與文學藝術,就足以在台灣新詩史上,佔有不朽的一頁。
台灣新文學運動,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涵,台灣新文化運動與中國五四運動的關係,則正如楊雲萍在〈台灣小說選〉的序所言:
台灣的新文學運動,是受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運動與成就所影響,所促進。既是台灣的運動,當然保持了多少的台灣特色。
而賴和本身易受相當程度的影響,賴和通過辛苦的創作歷程,因應日治下台灣的環境,從「中原文學」的源流,開創了台灣新文學的一片新天地。誠如上述,賴和先以中國白話文寫作,加上一些台灣語調,以加重台灣色彩,自然具有台灣意識,爾後本土色彩越來越重,弱小民族意識也漸呈現出來,還是在日本高壓統治下的必然回應。賴和在〈飲酒〉一詩中言:「我生不幸為俘囚,豈關種族他人
優;弱肉久以恣強食,致使兩間平等失。」台灣因滿清政府的積弱不振,致使其成為替罪羔羊,淪為弱小民族,而賴和正是承受著民族的悲哀寫作。
賴和的新文學經過我們從他的遺稿及己刊稿的一番清理,回復他的原始面貌。通過他的文學歷程,我們深刻感受,在日治時期,賴和以他的文學作品,為時代留下了「真正的印象」( true impression ) ,並給予極為強烈的文學控訴,充分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之聲。這是寶貴的文學遺產,不僅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中佔有主導的作用,也是五四文學革命的具體實踐,並且由於當時台灣直接處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,他的文學表現也更為強烈、深刻、動人;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,也相對的反映了文化啟蒙期的進步意識,我們有理由給予賴和崇高的評價,並需反省其所處的位置。